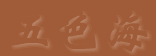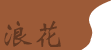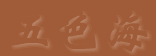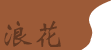| |
禅的修行
禅宗修行的目的在于获得洞悉事物本质的新观点。如果各位
屈从于二元论的规定而形成了条分缕析的逻辑思维习惯,我劝大
家还是尽量摆脱这种习惯,这样才能多少接近禅的观点。虽然各
位与我同住于一个世界,然而这个窗外的石头——我们只是习惯
地称呼它为石头——对于我们各人来说真是同一个石头吗?各位
啜一杯茶,我也啜一杯,行为似乎一样,但是在我们各自的一杯
茶中,心境却不一样,有人的一杯茶里并没有禅意,而有人的一
杯茶里却禅意盎然。这原因并不是外在的,因为一个人在逻辑理
性的圆周内辗转,而另一个人却站在逻辑理性之外。所谓禅宗的
新观点中其实并没有什么新东西,但是“新”这一语词却能表达
禅宗观点的特性,所以比我们使用“新观点”这个词,用禅宗的
话来说,这是“退一步”的表达方式。
获得新观点在禅宗叫“悟”,无悟则无禅,因为禅的生活是
从“悟”开始的。“悟”可以定义为与理性逻辑理解相对的直觉
性洞察。但我们先不必拘泥于定义如何,“悟”意味着在二元论
的思维方式中被隐没的、至今未被注意到的新世界的敞开呈现。
请记住上面所说的这一点,并看一看下面的禅语录,我想,各位
会明白“悟”究竟是什么。
初人丛林的一个僧人向赵州请教“心要”,赵州问:
“吃粥了也未?”
僧人答:“吃粥了也。”
赵州应声说道:
“洗钵盂去。”
于是僧人突然大悟。
对此,云门评论道:赵州这番话中有什么特殊涵义吗?如果
有,那是什么?如果没有,那么这个僧人又悟出了什么?但翠岩
则反驳云门说:云门禅师理解得也不干净利落,所以这样评说,
完全是画蛇添足,在宦官脸上添须。我以为,这个僧人没悟个什
么,只是栽入地狱而已!
赵州的“洗钵盂去”,僧人的“悟”,云门的选言判断,翠岩
的断语——这些究竟意味着什么?是互相贬损,或只是大惊小
怪?依我看来,它们都是指示着一条路。无论上述僧人向何处
去,他的悟当然也绝不是徒劳。
德山是《金刚经》的权威,有一次偶尔听说禅宗不立文字、
直指人心之说,便到龙潭那里请教。一天夜里,德山在门外打坐
思索禅的奥秘,龙潭问:
“何不入内?”
“因为里边真暗。”
龙潭便点烛给德山,德山刚接过,龙潭一口吹灭。当下德山
心灵豁然大悟。
百丈陪其师马祖外出,偶然见野鸭子飞,马祖问:
“是什么?”
“野鸭子。”
“甚处去也?”
“飞过去也。”
马祖突然扭住百丈的鼻头,百丈负痛失声,马祖说:
“纵然如此仍道飞过去了么?不是一直在这里吗?”这一句话
使百丈背上冷汗顿出,于是大悟。
洗钵、吹烛、扭鼻,这之间有什么联系,我们要依照云门大
师说:“如果没有,那么他们为什么悟到了禅的真理?如果有,
那么这之间的内在联系又是什么?而这悟又是什么?这是什么样
的新观点?”
宋朝的禅师大慧手下有个叫道谦的和尚,多年习禅却未能开
悟,他十分绝望。他常常被任命为使者派往远方城市,在路上要
奔波半年,他想,这更会妨碍他研究禅理。他的朋友宗元对他很
同情,说了如下劝慰的话:
“我也和你一起去,虽然我仅有微力,但会尽力帮助你,即
使一边赶路,也可以一边用功。”.
一夜,道谦哭诉道,愿请他帮忙解决一生的心事,宗元说:
“途中可替的事我尽替你,只有五件事替你不得,你须自家
支当。”
道谦恳切地问其详,宗元说:
“着衣、吃饭、屙屎、放尿、驮个死尸路上行。”
道谦当下领悟,不觉手舞足蹈,于是,宗元便告别:
“你此回方可通书,宜前进,吾先归矣。”
道谦便一人继续前行。半年后,他完成使命回到寺里,正巧
大慧偶然下山,路上碰见,大慧看着道谦的脸,说:
“你这回别也。”
试问,友人宗元向道谦说了那番恳切的忠告后,道谦心头闪
现出的是什么?
香岩是百丈的弟子,百丈去世后,他到同辈的沩山那里去,
沩山问他:“我听说你在百丈先师那里聪明伶俐,但靠这种聪明
伶俐得到的‘禅’,不外乎是出自理性分析的理解,而这恰恰是
堕人生死之路的根本原因,虽说如此,你也算参得些禅理的人
了,那么试以一句话说出:父母未生前,你自身是什么?”
香岩无言以对,茫然退出,回到宿舍后把先师讲录与其他典
籍翻出一一检寻,但怎么也找不到一句合适的答语,于是他又回
去向沩山反复讨教,沩山只说:“其实我也没有教你的,如果你
这样仿效我,日后你总有一天要骂我,即使我有什么可说给你
的,那也是我的而不是你的。”香岩沮丧之极,便埋怨沩山的生
硬,并决心把历来熟读的而今却不能帮助自己的书籍统统烧掉,
并暗下决心:
“一生再也不学这难解又不可教的佛法了,且作个长行粥饭
僧,免劳心神。”
他辞别沩山,到南阳忠国师旧居结庵而住。一天扫地时,扫
帚偶然碰到瓦砾,飞起的瓦砾击中竹子,发出清脆的响声,他突
然省悟,理解起来没有丝毫滞碍,那正是与亡故的父母重逢的意
愿哩!不仅如此,他对沩山拒绝明确示教的缘由也有了深入的理
解,他清醒地意识到,如果沩山对他并不真心,而是教给了他什
么的话,那么他永远也得不到这一体验了。
禅宗不是靠师父的说明令弟子开悟的,悟决不允许有理性的
分析,因此,它是无论如何反复说明论证都不能传达给体验者之
外的任何人的经验。如果靠分析能使人明白、理解,靠说明能够
表达、传递,那么这“悟”不成其为“悟”,而变成了概念的
((J晤”,是僵死的东西,在那里已没有了禅的体验了。因此,禅师
训导所能做的唯一的工作,就是指示其注意的目标,暗示其可行
的途径,而要达到目标,则必须由本人自行去做,谁也代替不
了。而所谓的“指示”或“暗示”,则随处皆是,信手可拈,当
悟的心机成熟,到处会撞见会心之物,微弱的声响,任何话语,
突然开放的花朵,无意中的跌跤等细琐小事,都成了使心灵彻悟
的契机,看上去微不足道的小事在某种意义上却产生了超越均衡
的结果,而悟的一切原因与条件都在于心灵。心灵只不过在等待
成熟的时机,一旦以某种原因在心灵中形成了这种时机,鸟飞、
铃响,只要有这样的契机就会忽然回归本来的故乡,发现本来的
面目,即原来从开始就没有任何遮蔽的东西,都会源源不断地呈
露在面前。所以在禅宗那里并没有什么需要说明、教导的东西,
惟从自身中产生。
宋代著名的儒学家、诗人、政治家黄山谷初到晦堂处学禅,
晦堂说:
“只如仲尼道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者,太史
居常,如何理论?”
黄山谷正准备回答,晦堂制止说:“不是,不是。”于是黄山
谷大惑不解,无言可对。此后,两人曾在山中散步,当时正好木
樨盛开,香气四溢,晦堂说:
“闻木樨花香么?”
“闻。”
“吾无隐乎尔。”
黄山谷于是恍然大悟。
在上述各例中,我想已经大体可以说明悟是什么,如何获得
悟了。但也许会问,“细读你的说明指示,仍有未尽明白处。假
如‘悟’总是有某种内容的,那么难道不能清晰地加以记述吗?
您举的事例和您的论说大多是心理意图性的,所以我们所明白的
仅仅是风的方向,而那只小船最终究竟应该停泊在哪个港口呢?”
对于这个问题,禅者会这样回答:在内容上,悟也罢,禅也
罢,凡是能被理性理解的可以证示、记述、提示的东西一概没
有。因为禅与概念没有关系,悟是一种内在的知觉——不是对个
别的对象的知觉而是对实在本身的知觉。悟的最后归宿是自身
(self),除了回归到自身之外别无他处。所以赵州说“吃茶去”,
南泉说“这茅镰子我使得正快”。自我正是这样运动的,如果要
把握它,就必须在这“运动”中去把握。
由于悟是直透存在底蕴的,所以获得悟常常是人生的转折
点,但必须是彻底的干脆的,那种沾皮带骨的“悟”比不悟还恶
劣,请看下面的例子:
临济挨黄檗三十棒时,一旦悟人,便全然不同了,“黄檗佛
法无多子”!这便是他新生的宣言。再见黄檗时,他便劈面一掌。
有人会想,这是多么傲慢无礼呀!可是临济这种粗暴行动却有着
他的充足理由,而黄檗也对这种寒暄方式颇感满意与欣慰。
德山一旦悟禅,便立即取《金刚经》的疏抄烧掉,那曾是他
最宝贵的东西,无论到哪里都背着,须臾不可离身的。但悟后他
却这样宣告:“穷诸玄辨,若一毫置于太虚;竭世枢机,似一滴
投入巨壑。”
前面曾提到过的关于“野鸭子”对话的第二天,马祖上堂说
法,百丈却走出来把为老师礼拜铺的坐具卷了起来。通常卷坐具
是说法结束的意思,马祖没有责怪,下坛回方丈去了。一会儿叫
百丈问道:
“我适来未曾说话,汝为甚便卷却席?”
“昨日被和尚扭得鼻头痛。”
“汝昨日向甚处留心?”
“鼻头今日又不痛了也。”
因此马祖认为百丈已经悟透了。
在上述例子中,我想可以说明由于悟的获得,心中发生了什
么变化了吧。在悟之前,僧人们是多么无力,他们好像在沙漠中
迷路的旅人,但一旦悟人,他们却如同一个绝对权威的君主王,
他们对谁也不再屈从,他们便是自身的主人!
此外,在这里有必要对“悟”这种心灵开发作几点回顾与总
结。
一、常常有人以为,禅宗修行是依靠冥想产生自我暗示状
态,这从我们上面所举的例子中可以证明是完全错误的。禅宗的
“悟”决不是依靠高度的思维集中,产生一定的预期的意识状态
的现象,而是新观点的获得。意识发生以来,我们总是用一定的
概念性分析性的方法去对应内外的各种条件,禅宗修行一举倾覆
了这个基础,使这个旧的骨架在全新的基础上重建。因此,在禅
宗里面,对相对性意识产物的形而上学性象征性命题的冥想是没
有立足之地的。
二、如果不能“悟”,那么任何人都不能参到禅宗的真理。
所谓“悟”,即在意识中突然闪现出过去连做梦也没有梦到过的
全新的真理,无论理性与论证堆积得多么深厚,在这一悟中,顿
时便会引起一场精神的大变化(catastrophe),堆积超过一定的
度,全部堆积物便会坍塌。这时你看!崭新的世界便豁然呈现,
水到了零度就会结冰,液体变为固体不再流动,“悟”在求道者
已感到绝望的极限时就会不期而至。从宗教角度来说它是新生,
从理性的角度来说它是获得新观点,人们会觉得世界如今焕然一
新,感到这新的世界甚至隐没了佛教称为“无明”的所有二元论
的丑恶。
三、悟是禅宗的存在价值(reason for being),没有悟,禅宗
便不是禅宗了,因此,禅宗训练、教育的全部力量都倾注于悟的
开发。禅宗并不把“悟”看作是自然会来的,即凭胡思乱想消极
等待也能等来的漫长过程,而是抱着拯救求禅弟子的热情,为迫
使他们进入非悟不可的绝境才提出那些似乎不可理解的问话来让
他们体验的。通常哲学、宗教的指导者所进行的理性辩证、谆谆
解说在这里都不能得到所期望的结果,弟子们为此而常常困惑不
解,这种现象在佛教携带着高度形而上的抽象概念及复杂的瑜伽
修行体系进入中国的初期格外普遍。因此,它使比较现实的中国
人对如何把握佛教的核心感到为难。菩提达摩、六祖慧能、马祖
道一、石头希迁以及其他中国禅师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因而禅
宗的形式与发展便是很自然的了。在他们的努力下,悟,被置于
对经典的研究之上,与禅成为一体,因此,无悟之禅如同没有辣
味的胡椒一样不可思议。当然,也有着应该叫做“过剩”的悟,
这是必须注意避免的。
四、在强调禅宗的“悟”的时候,应该注意的是,禅宗的禅
与印度佛教、中国佛教其他宗派所奉行的“禅那”体系是不同
的,通常说到“禅那”,是指那种指向一定思想内容的冥想或疑
心。这思想内容,在小乘佛教常常是“无常观”,在大乘佛教常
常是寻求“空”,当心灵被训练到意识甚至无意识的感觉都消失,
出现了完全的空白状态的时候,换句话说,即所有形式的心灵活
动都从意识中被排除出去,心灵中一丝云彩也没有,只剩下广袤
蔚蓝的虚空的时候,可以说“禅那”便到达成功了,这可以称之
为迷醉(ecstasy或extasy)或梦幻般境界(trance),但不能称之
为禅宗的禅。禅宗的禅必须“悟”,必须是一气推倒1日理性作用
的全部堆积并建立新生命基础的全面的心灵突现,必须是过去从
未有过的通过新视角遍观万事万物的新感觉的觉醒。而“禅那”
之中并没有这个意思,因为它不过是使心灵归于宁静的训练,当
然这是禅那的长处,但尽管如此,也不能把它与禅宗的禅等同看
待。
五、悟,绝不是基督教神秘主义者所主张的那种“如实观
神”,而是一种透人创造性活动,观察创造主体自身的方式,禅
宗一开始就明白地提倡这种方式。造物主也许忙于宇宙形成的工
作,也许正在休息。但禅宗却不停地在探索着自身的运动,并不
依赖什么造物主的支持,在人生中把握人生,禅宗得到了满足。
五祖山的法演,常常伸出自己的手问:“这是谁的手?”我们如果
明白了其中的缘由,也就有了悟与禅。而神秘主义想象神灵,则
无论如何也要设置一个特定的对象。把握了神,便排斥了非神,
这是通常思维限定作用的必然结果。而禅宗则要求绝对自由,甚
至向神要求自由,“无所住”便是这个意思,“说佛也须漱口”也
是这个意思。不能把禅宗看成是病态的对神的不虔敬或无神论,
它只是认为,仅仅有名称概念是不完全的,正因为如此,药山在
说法时一言不发下坛归方丈(室),而百丈则只是走出两三步向
人们摊开双手,这实际上不是已经透露了其间的秘义吗?
六、悟,不是常被作为异常心理来研究病态意识的好题目,
如果要说它是什么,毋宁说它是最正常的意识。当说它是“心的
凸现”等时,也许有人会认为禅宗逃避做普通人。这种看法是荒
谬的,但不幸的是常常有些被先人之见笼罩了的批评家却支持这
一见解。正如南泉所说,禅是“平常心”的,如同大门向里开还
是向外开只是合页装法的差异一样,在一瞬间事态转换,禅就能
成为各位自身的东西,而各位仍然和过去一样完全正常。不仅如
此,在那一瞬间,各位获得了某种全新的生命,整个精神都建立
和活动在全然不同的基调中了,那是一种从未经验过的满足、平
和与喜悦的境界。人生的基调为之一变,禅悟使生命活力苏醒,
春天的花朵更加可爱,溪流的水更加清冽,得到这样的全新感
觉,怎么能说是“异常”?!应该说,当人生越发深刻地品尝到它
的滋味,当人生的广阔包容了全宇宙的时候,就会明白悟中有极
其珍贵、值得全力追求的某种东西。
《六祖坛经》大义——钱 穆
在后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有两大伟人,对中国文化有其极大
之影响,一为唐代禅宗六祖慧能,一为南宋儒家朱熹。六祖生于
唐太宗贞观十二年,卒于玄宗先天二年,当西历之七世纪到八世
纪之初,距今已有一千两百多年。朱子生于南宋高宗建炎四年,
卒于宁宗庆元六年,当西历之十二世纪,到今也已七百八十多
年。慧能实际上可说是唐代禅宗的开山祖师,朱子则是宋代理学
之集大成者。一儒一释开出此下中国学术思想种种门路,亦可谓
此下中国学术思想莫不由此两人导源。言其同,则慧能是广东
人,朱子生卒皆在福建,可说是福建人,两人皆崛起于南方,此
乃中国文化由北向南之大显例。言其异,慧能不识字,而朱子博
极群书,又恰成一两极端之对比。
学术思想有两大趋向互相循环,一日积,一日消。孟子曰:
“所存者神,所过者化。”存是积,化是消。学术思想之前进,往
往由积存到消化,再由消化到积存。正犹人之饮食,一积一消,
始能营养身躯。同样,思想积久,要经过消化工作,才能使之融
会贯通。观察思想史的过程,便是一积一消之循环。六祖能消能
化,朱子能积能存。所以中国传统文化的儒释融合,如乳投水,
经慧能大消化之后,接着朱子能大积存,这二者对后世学术思想
的贡献,也是相辅相成的。
自佛教传人中国,到唐代已历四百多年,在此四百多年中,
求法翻经,派别纷歧。积存多了,须有如慧能其人者出来完成一
番极大的消的工作。他主张不立文字,以心印心,直截了当的当
下直指。这一号召令人见性成佛,把过去学佛人对于文字书本那
一重担子全部放下。如此的简易方法,使此下全体佛教徒,几乎
全向禅宗一门,整个社会几乎全接受了禅宗的思想方法,和求学
路径,把过去吃得太多太腻的全消化了。也可说,从慧能以下,
乃能将外来佛教融人于中国文化中而正式成为中国的佛教。也可
说,慧能以前,四百多年间的佛教,犯了“实”病,经慧能把它
根治了。
到了宋代,新儒学兴起,诸大儒如周敦颐、程颢、程颐、张
载诸人,他们都曾参究佛学,其实他们所参究的,也只以禅宗为
主。他们所讲,虽已是一套新儒学,确乎与禅宗不同。但平心而
论,他们也似当时的禅宗,同样犯了一个虚病,似乎肚子吃不
饱,要待朱子出来大大进补一番。此后陆、王在消的一面,明末
顾、王诸大儒,在积的一面。而大体说来,朱子以下的中国学术
界,七八百年间,主要是偏在积。
佛教有三宝,一是佛,一是法,一是僧。佛是说法者,法是
佛所说,但没有了僧,则佛也没了,法也没了。佛学起于印度,
而后来中断了,正因为他们没有了僧,便亦没有了佛所说之法。
在中国则高僧大德,代代有之,绵延不绝,我们一读历代高僧传
可得其证,因此佛学终于成为中国文化体系中之一大支。而慧能
之贡献,主要亦在能提高僧众地位,扩大僧众数量,使佛门三
宝,真能鼎足并峙,无所轩轾。
让我们再来看一看当前的社会,似乎在传统方面,已是荡焉
无存,又犯了虚病。即对大家内心爱重的西方文化,亦多是囫囵
吞枣,乱学一阵子,似乎又犯了一种杂病,其实质仍还是虚病。
试问高唱西化的人,哪几人肯埋首翻译,把西方学术思想,像慧
能以前那些高僧们般的努力,既无积,自也不能消。如一人长久
营养不良,虚病愈来愈重。此时我们要复兴中国文化,便该学朱
子,把[日有的好好地积存。要接受西方文化便该学慧能,把西方
的能消化融解进中国来。最少亦要能积能存。把西方的移地积存
到中国社会来,自能有人出来做消化工作。到底则还需要有如慧
能其人,他能在中国文化中消化佛学,自有慧能而佛学始在中国
社会普遍流传而发出异样的光彩。
讲佛学,应分义解、修行两大部门。其实其他学术思想,都
该并重此两部门。如特别着重在义解方面而不重修行,便像近世
中国高呼西化,新文化运动气焰方盛之时,一面说要全部西化,
一面却又要打倒宗教,不知宗教亦是西方文化中一大支。在此潮
流下,又有人说佛教乃哲学,非宗教,此是仅重义解、思辨,却
蔑视了信奉修行。两者不调和,又成为近代中国社会一大病痛。
稍进一层讲,佛教来中国,中国的高僧们早已不断在修行、
义解两面用力,又无意中不断把中国传统文化渗进佛教,而使佛
法中国化。我且举一慧能以前的竺道生为例。竺道生是东晋南宋
间人,他是第一个提倡顿悟的。所谓“顿悟”我可简单把八个字
来说,即是:“义由心起,法由心生。”一切义解,不在外面文字
上求,都该由心中起。要把我心和佛所说法迎合汇一,如是则法
即是心,心即是法,但须悟后乃有此境界,亦可谓得此境界乃始
谓之悟,悟到了此境界,则佛即是我,我即是佛。信法人亦成了
说法人。如竺道生说一阐提亦得成佛,明明违逆了当时已译出之
《小品泥洹经》之所云。但竺道生却说,若我错了,死后应人拔
舌地狱;若我说不错,则死后仍将坐狮子座宣扬正义。此后慧能
一派的禅宗,正是承此“义由心起,法由心生”之八字而来。
此前佛门僧众,只知着重文字,宣讲经典,老在心外兜圈
子,忽略了自己根本的一颗心。直到不识一字的慧能出现,才将
竺道生此一说法付之实现,固然竺道生是一博学僧人,和慧能不
同,两人所悟亦有不同,然正因为竺道生之博学,使人认为其所
悟乃由一切经典文字言说中悟,惟其慧能不识一字,乃能使人懂
得其悟乃不自一切经典文字言说中悟,而实由心悟,而禅宗之顿
悟法乃得正式形成。
今天我将偏重于慧能之“修”,不像一般人只来谈他之悟。
若少注意到他的修,无真修,又岂能有真悟?此义重要,大家应
注意。慧能是广东人,在他时代,佛法已在中国渐渐地普及民
间,佛法从两条路来中国:一从西域到长安,一从海道到广州。
当慧能出世,在广州听闻佛法已早有此机缘。
据《六祖坛经》记载,慧能是个早岁丧父的孤儿,以卖柴为
生,他亦是一个孝子,以卖柴供养母亲。一日背柴到城里卖,听
人念《金刚经》,心便开悟。此悟正是由心领会,不藉旁门。慧
能便问此诵经人,这经从何而来,此人说:是从湖北黄梅县东山
禅寺五祖那里得来。但慧能身贫如洗,家有老母,要进一步前去
听经是不易之事,有人出钱助他安置了母亲,独自上路前往黄
梅。我们可说,他听到其人诵《金刚经》时是初悟,此后花了三
十余天光阴从广东到黄梅,试问在此一路上,那时他心境到底如
何?他自然是抱着满心希望和最高信心而前去,这种长途跋涉的
艰苦情况,无疑是难能可贵的。我们可想知他在此三十余天的路
程中,实有他的一番修,此是真实的心修。
到了黄梅,见到五祖弘忍,弘忍问他:“你何方人,前来欲
求何物?”他说:“惟求作佛,不求余事。”这真是好大的口气呀!
请问一个不识字人如何敢如此大胆?当知道这正与他三十余天一
路前来时的内心修行有大关系,不是临时随口能出此大言。他那
时的心境,早和在广东初闻诵《金刚经》时,又进了一大步,此
是他进一步之悟。
当时弘忍再问:“你是岭南人,又是獠猫,若为堪作佛?”他
答说:“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獠猫身与和尚不同,佛性
有何差别。”此一语真是晴天霹雳,前无古人,想见慧能一路上
早已自悟到此。在他以前,固是没有人说过,在他之后,虽然人
人会说,然如鹦鹉学舌,却不能如慧能般之由心实悟。弘忍一听
之下,便知慧能不是泛泛之徒,为使他不招意外,故将明珠暗
藏,叫他到后院去做劈柴舂米工作。慧能眼巴巴自广东遥远来黄
梅,一心为求作佛,却使他去厨下打杂做粗工,这是所为何来?
但他毫不介意,天天在厨下劈柴舂米,此时他心境应与他到黄梅
初见五祖心境又大不同,这些工作,好像与他所要求的毫不相
干,其实他亦很明白,五祖叫他做此杂工,便正是叫他“修”,
也便是做佛正法啁!
慧能在作坊苦作已历八个月,一天,弘忍为要考验门下众僧
徒工夫境界,叫大家写一偈子,自道心得,大家都不敢写,只有
首座弟子神秀不得不写,在墙壁上写一首偈说: “身是菩提树,
心是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这首偈却又不敢直陈
五祖,但已立时传遍了东山全寺,也传到了慧能耳中,慧能一时
耐不住,也想写一偈,但不识字,不能写,只好口念请人代笔写
道:“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我
们又当知,此“本来无一物”五字,正是他在磨坊中八个月磨米
中磨出来的,只此一颗清清净净的心,没有不快乐,没有杂念,
没有渣滓,没有尘埃,何处再要拂拭?此正是慧能自道心境,却
不是来讲佛法。此时则已是慧能到家之悟了。
五祖弘忍见了慧能题偈,对于他身后传法之事,便有了决
定,他到磨坊问慧能:“米熟了没有?”答称:“早已熟了。”弘忍
便以杖击碓三下,背手而去。有这老和尚这一番慈悲心与其一代
宗师之机锋隐语,配上慧能智慧大开,心下明白。叫他劈柴就劈
柴,教他舂米就舂米,不折不扣,潜心暗修,时机一到,便知老
和尚有事要他去,他便于三更时分,由后门进入老和尚禅房,弘
忍便把宗门相传衣钵付给与慧能,嘱他赶快离开黄梅以防不测,
慧能说:深夜不熟路径,五祖遂亲自把他送到江边,上了渡船,
离开了黄梅。我们读《坛经》看他们师弟间八个月来这一番经
过,若不能直透两人心下,只在经文上揣摩,我们将会是莫明其
妙,一无所得。由上说来,我们固是非常佩服六祖,亦不能不佩
服到五祖。但五祖也不是一个博学僧人呀!
两个月后,六祖到了大庾岭,但在黄梅方面,衣钵南去的消
息也走漏了,好多人想夺回衣钵,其中一个脚力健快,赶到大庾
岭见到了慧能,所谓:善者不来,来者不善,这位曾经是将军出
身的陈慧明追赶六祖的目的,无非是在衣钵上。即时六祖便把衣
钵放置石上,陈慧明拿不动衣钵,转而请教六祖,问:“如何是
我本来面目?”六祖说:“你既然为法而来,可屏息诸缘,勿生一
念。”良久又说:“不思善,不思恶,正与麽时,哪个是明上座本
来面目?”慧明言下大悟。
这是《坛经》的记载,但以我个人粗浅想法,慧能本不该把
五祖传授衣钵轻易交与慧明,可是逼于形势,又属不能坚持,所
以置之石上,意谓:我并无意把衣钵给你,你如定要强抢,我也
不作抗拒。另一方面的慧明,本意是在夺回衣钵,待一见衣钵置
于石上,却心念一转,想此衣钵不好夺取,所以又转向他自己本
来面目,这正由要衣钵与不要衣钵这一心念转变上来请问。若说
衣钵在石上,慧明拿不动,似乎是故’神其辞,失去了当时的实
况,但亦同时丧失其中一番甚深义理,这也待我们心悟其意的人
来善自体会了。我们当知,见衣不取,正是慧明心中本来面目,
而慧能此一番话,则成为第一番之初说教。
慧能承受衣钵之后,又经历了千辛万苦,他自说那时真是命
如悬丝。他是一不识字人,他在东山禅寺,也未正式剃发为僧,
他自知不得行化太早,所以他只是避名隐迹于四会猎人队中,先
后有十五年之久。每为猎人守网,见到投网的生命,往往会为它
们放出一条生路。又因他持戒不吃荤,只好吃些肉边莱。慧能在
此漫长岁月中,又增长了不少的潜修工夫。比之磨坊八月,又更
不同。
后来到了广州法性寺,听到两个僧人在那里争论风动抑是幡
动,慧能想,我如此埋藏,终不是办法,于是他上前开口说:
“不是风动,不是幡动,而是仁者心动。”此语被该寺座主印宗听
到,印师也非常人,早已传闻五祖衣钵南来,如今一听慧能出
语,便疑他是受五祖衣钵的人。一问之下,慧能也坦白承认了。
诸位又当知,此“仁者心动”四字,也并不是凭空说的,既不如
后来一般禅师们之浪作机锋,也不如近人所想,如一般哲学家们
之轻肆言辩。此乃慧能在此十五年中之一番真修实悟。风动幡
动,时时有之,命如悬丝,而其心不动,这纯是一掴一掌血的生
派经验凝炼而来。慧能只说自己心情,只是如实说法,不关一切
经典文字。自五祖传法,直到见了印宗,在此十五年中,慧能始
终还是一个俗人身份,还没有比丘的具足戒。自见印宗后,才助
他完成了出家人和尚身份。此下才是他正设教度人的开始。
六祖不识字,在他一生中所说法,只是口讲给人听,今此一
部《六祖坛经》之所有文字,乃是他门人之笔录,他门人也把六
祖当时的口语,尽量保持真相,所以《六祖坛经》乃是中国第一
部白话作品,宋朝两代理学家之语录,也是受了此影响。依照佛
门惯例,佛之金口说法始称“经”,菩萨们的祖述则称“论”。只
有慧能《坛经》却称“经”,此亦是佛门中一变例,而且是一大
大变例,这一层,我们也不该忽略过。若说《坛经》称“经”,
不是慧能之意,这又是一种不必要的解说。
我们必要明白了慧能东山得法此一段前后十六年之经过,才
能来谈慧能之《坛经》。《坛经》中要点固多,但在我认为,所当
注意的以下两点最重要。
其一,是佛之自性化。竺道生已说,一切众生都有佛性,此
佛性问题不是慧能先提出,慧能讲“心即是佛”,反转来说则成
为佛即是心。此与竺道生所说也有些区别。慧能教我们见性成
佛,又说言下见性,又说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自性能含万
法,万法在人性中。能见性的是我此心。故说万法尽在自心,何
不从9Jb中顿见真如本性。他说:但于此心常起正念,烦恼尘劳
常不能染,即是见性。又说:能识自心见性,皆成佛道。他强调
自修心、自修身,自性自度。又说自修自成佛道,此乃慧能之独
出前人处,亦是慧能所说中之最伟大最见精神处。
其二,是佛之世间化。他说“万法皆由人与”,“三藏十二部
皆因人置”。“若无世人,一切万法本自不有”。“欲求见佛,但识
众生,不识众生,则万劫觅佛难逢”。这样讲得何等直截痛快!
总而言之,慧能讲佛法,主要只是两句话,即是“人性”与
“人事”,他教人明白本性,却不教人摒弃一切事。所以他说:
“恩则孝养父母,义则上下相怜,让则尊卑和睦,忍则众恶无
喧。”所以他又说, “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又说:
“在家能行,如东方人心善,在寺不修,如西方人心恶。”又说:
“自性西方。”他说:“东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
念佛,又求生何国?”又说: “心平何用持戒,行直何用修禅。”
这些却成为佛门中极革命的意见。慧能讲佛法,既是一本心性,
又不摒弃世俗,只求心性尘埃不惹,又何碍在人生俗务上再讲些
孝悌仁义齐家治国。因此唐代之有禅宗,从上是佛学之革新,向
后则成为宋代理学之开先,而慧能则为此一大转捩中之关键人
物。
现在我再讲一则禅门寓言来作此文之结束。那寓言云:有一
百无一失的贼王,年老预备洗手不干了,他儿子请老贼传授做贼
技巧。某夜间,老贼带他儿子到一富家行窃,命儿上楼人室,他
却在外大叫捉贼,主人惊醒,儿子无法,躲人柜中,急中生智,
故自作声,待主人掀开柜门,他便一冲逃走。回家后,埋怨老
贼,这时贼王却向他说,你可以单独自去作贼了。这是说法从心
生,真修然后有直悟。牢记这两点,却可帮助我们了解慧能以下
禅门许多故事和其意义之所在。
禅悟与精神分析——[美]弗洛姆——洪修平 译
禅的目标是悟:对实在作直接的、非反思的把握,没有感情
的污染与理智化,清楚地了解到自己与宇宙的关系。这个新的体
验是儿童前智力的、直接的把握之重复,但这是在新的层次上的
重复,它是人的理性、客观性与个性的充分发展。而儿童的直接
与同一的体验,是在异化与主一客体分裂的体验之前的,悟的体
验则在它之后。
精神分析的目标,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是使无意识成为意
识,是用自我来代替本我。确实,所要发现的无意识之内容只限
于人格的很小一部分,即是那些存在于儿童早期,而后又被遗忘
了的那些本能冲动。把这些冲动从压抑状态中解放出来,这就是
精神分析法的目标。此外,所要发现的那些无意识都决定于治疗
具体病症的需要——这实际上完全离开了弗洛伊德的理论前提。
对于那些与症状无关的无意识,则很少关心。近年来,对死亡本
能、生存本能等概念的引入以及对自我各个方面的发展,才使弗
洛伊德无意识内容的概念逐渐地有所扩大。非弗洛伊德的各个学
派极大地扩展了有待发现的无意识部分。最激进的是荣格,但阿
德勒、兰克以及最近一些所谓新弗洛伊德主义著作家,也都对这
种扩展作出了贡献。但是(除了荣格),尽管扩大了范围,这些
扩大的方面却仍然决定于治愈这种或那种症状的治疗目标,或决
定于治愈这种或那种神经症性格特性的治疗目标。它没有包括整
个的人。
然而,如果我们沿着弗洛伊德的最初目标——使无意识成为
意识——推到它的最后结论,那么,我们一定会使它摆脱弗洛伊
德自己的本能定向以及治愈症状的直接任务强加于其上的限制。
如果我们追求无意识的充分恢复这个目标,那么,任务就不限于
本能,也不限于其他有限的体验,而是在于整个人的整个体验;
那么,目标就变为克服异化、克服在认识世界时的主一客体分
裂,那么,无意识的发现就意味着克服感情污染和大脑思考;它
意味着压抑之解除,我自身内部普遍的人与社会的人的分裂之消
除;它意味着意识与无意识对立的两极之消失;它意味着到达对
实在的直接把握状态,没有扭曲,没有理智反思的干扰;它意味
着克服执著自我、崇拜自我的癖好;它意味着放弃一个不灭的独
立的自我之幻想,这个自我想要被扩大、被保存,就像埃及的法
老希望将自身保存为木乃伊以求永恒一样。意识到无意识,意谓
开放、反应,并非有任何东西,而就是“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