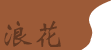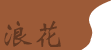| | 禅宗中国化有一特点:各取所需,淘汰其余。印
度传来的佛经不下千卷,万卷,有几千种,不但普通人念不懂,
连老和尚有许多也不能读懂。我一生碰到过和尚有六十万人,只
有三、四个自称饱读佛经,一般和尚只念一本、二本,而禅院的
和尚一本都不念!只要有一句话能解决问题,他们就以之实践下
去。因此,接受外国思想不能盲目接受,而应该明白你自己最需
要什么,找到你最有用的、最受启发性的东西,把它拿来进行实
践,并不断深刻化,系统化,解决你的问题。这也是中国佛学的
一个特点,即选择性。这并非说佛教中国化过程完全是选择性
的,亦有综合性在内。一般来说,中国佛教哲学是通过综合性来
达到建立系统,实践中的佛学是通过选择性的,禅宗是实践性
的,因此是选择性的。
再说一点,禅宗在中国的成功,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没有起破
坏或钳制作用。中国讲的佛法,在道家庄子那里有,在儒家那里
也有一点儿。因此,禅宗对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亦吸收其精华,也
是选择性的,能采用的就采用,不用的,摆在那儿,也不把它烧
掉。
最后,禅宗在中国化过程中非常注重实践。一个人,要相信
真理,真理唯一标准:看它是否能在实际生活中解决问题。禅宗
正是抓住了这一点。他不重印度所讲的繁琐的一套,而看在实际
中能否解决问题,只要能解决问题,什么办法都可以。
从印度禅到中国禅转变的过程,佛法中国化过程中,我想我
们能吸收许多很有益的经验,这对中国搞现代化,如何吸收外来
文化,而又保持住自己的文化能提供一榜样。
试论唐末以后的禅风——巨 赞
禅宗发展至唐末,禅师们在上堂、小参、拈古、勘辨时所用
的语句,大都讲究修饰,有时还用对偶很工整的韵文,如唐懿宗
咸通年间,有僧问夹山灵泉禅院的善会禅师“如何是夹山境”?
善会答道:“猿抱子归青嶂里,鸟衔花落碧岩前。”,禅境诗情,极
为浓郁,因而传诵一时,夹山也被禅子们称为“碧岩”。其后数
十年,法眼文益禅师在《宗门十归论》里说:
稍睹诸方宗匠,参学上流,以歌颂为等闲,将制作
为未事。任情直吐,多类于野谈;率意便成,绝肖于俗
语。自谓不拘粗犷,匪择秽孱,拟他出俗之辞,标归第
一主义。识者览之嗤笑,愚者信之流传,使名理而寝
消,累教门之愈薄。不见《华严》万偈,祖颂千篇,俱
烂漫而有文,悉清纯而靡杂,岂同猥俗,兼糅戏谐。在
后世以作经,在群口而为实,亦须稽古,乃要合宜。苟
或乏于天资,当自甘于木讷,胡必强攀英俊, 希慕贤
明,呈丑拙以乱风,织弊讹而贻戚,无惑妄诞, 以滋后
羞。 。
一代宗师,这样竭力提倡语句的修饰,自然会影响禅风(宗门的
风气),而法眼自己也经常用诗偈说法。如《冷斋夜话》卷一云:
“宋太祖将问罪江南,李后主用谋臣计,欲拒王师。 法眼禅师观
牡丹于大内,因作偈讽之曰:‘拥毳对芳丛,由来趣不同。发从
今日白,花是去年红。艳冶随朝露,馨香逐晚风。何须待零落,
然后始知空。’后主不省,王师旋渡江。”这段记载艾口果是实在的
话,则法眼不但以诗偈谈禅,而且又以之论政,在这样的场合,
语句当然非讲究修饰不可了。
法眼圆寂之后二三十年,汾阳善昭禅师创为颂古,在上堂、
小参等方面所用的诗偈就更多。《补续高僧传》卷六云:
颂古自汾阳始,观其颂布毛公案曰:“侍者初心慕
胜缘,辞师拟去学参禅;鸟窠知是根机熟,吹毛当下获
心安。”与胡僧金锡光偈,看他吐露,终是作家,真实
宗师,一拈一举,皆从性中流出,殊不以攒华叠锦为贵
也。
其实,在《汾阳无德禅师语录》里诗歌偈颂占了三分之二的篇
幅,真可以说是“烂漫有文,清纯靡杂”了。
稍后于汾阳的雪窦重显禅师,素以“工翰墨”见称,他在未
悟道的时候追慕诗僧禅月贯休,有诗云:“红芍药边方舞蝶,碧
梧桐里正啼莺。离亭不折依依柳,况有青山送又迎。”造句清新,
意境深密,的是诗中上品。他得法于云门宗的智门光祚禅师之
后,意境更高,造句更奇,如他在就任雪窦寺住持的时候,上堂
云:“春山叠乱青,春水漾虚碧。寥寥天地间,独立望何极。”气
韵高卓,似有过于善会禅师的答“夹山境”。
云门宗的开山祖师文偃禅师,气象阔大,机锋迅利。法眼禅
师在《宗门十规》里以“函盖截流”四字称颂他。“函盖”就是
云门“三句语”中的“函盖乾坤”。缘密禅师(云门的弟子)颂
云:“乾坤并万象,地狱及天堂。物物皆真现,头头总不伤。”是
就体上说的。“截流”也就是“截断众流”,缘密颂云:“堆山积
岳来,一一尽尘埃。更拟论玄妙,冰消瓦解摧。”是就用上说的。
体上一切现成,用上纤尘不立。云门说法,雷奔风卷,纵横变
化,总不出此范畴,而具体表现在他的“一字禅”上。可是他的
语句,有时不免像法眼所非议的“野谈”或“俗语”,当时有人
嫌他“太粗生”。二传至智门光祚禅师则有所改进,如智门颂文
殊白椎公案云:“文殊白椎报众知,法王法令合如斯。会中若有
仙陀客,不待眉间毫相辉。”格律声韵都很工稳。雪窦久受智门
的熏陶,又受了汾阳等人的影响,他的文学天才和宗门悟境就融
结为《颂古百则》,成为法眼所说“歌颂制作”的典型。
《颂古百则》所引用的公案,除《楞严经》二则、《维摩经》
一则、《金刚经》一则外,其余九十六则中,以云门宗的公案为
重点,云门文偃禅师一人的公案共有十五则,就是一个证明。至
于理境,也像他的其余六种著作一样(雪窦有《洞庭语录》、《雪
窦开堂录》、《瀑泉集》、《祖英集》、《颂古集》、《拈古集》、《雪窦
后录》七种),发扬了“函盖截流”的主旨。所以《补续高僧传》
卷七说:“云门一宗,得雪窦而中兴。”可是雪窦的《颂古百则》
得到临济宗杨歧派的圆悟克勤禅师在住持夹山灵泉禅院时,加上
评唱,组成《碧岩录》(或称《碧岩集》),而被当时的禅僧们称
为“宗门第一书”。这一事实说明,禅宗从唐末发展至北宋,不
但在语句的修饰上达到了空前成熟的程度,而且在宗派之间也倾
向于合流。
《续传灯录》卷七《杨岐方会禅师传》中云,“其提纲振领,
大类云门”。又宋高宗绍兴三年耿延禧《圆悟佛果禅师语录·序》
云,“佛以一音而演说法,故一切法,同此一音。三世诸佛此一
音,六代祖师此一音,天下老和尚此一音。……昔杨岐以此音鼓
簧天下,至圆悟大禅师,此音益震”,可见临济宗的圆悟禅师根
据云门宗雪窦禅师的颂古,加以评唱,乃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续传灯录》卷二十五《克勤禅师传》云:
会部使者解印还蜀,诣祖(法演)。祖曰:提刑少
年曾读小艳诗否?有两句颇相近,“频呼小玉元无事,
只要檀郎认得声”,提刑应喏喏。祖曰:且子细。师适
归侍立次,问曰:闻和尚举小艳诗,提刑会否?祖曰:
他认得声。师曰:“只要檀郎认得声”,他既认得声,为
甚么却不是?祖曰: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庭前柏树子!
墅师忽有省,遽出,见鸡飞上栏干鼓翅而呜,复自谓
曰:此岂不是声!逐袖香入室通所得,呈偈曰: “金鸭
香销锦绣帏,笙歌丛里醉扶归。少年一段风流事,只许
佳人独自知。”祖曰:佛祖大事,非小根劣器所能造诣,
吾助汝喜。祖遍谓山中耆旧曰:我侍者参得禅也。
圆悟从小艳诗悟人,悟后诗偈深得诗中三昧,可见也是一个极有
文学天才的人。他引雪窦为同调,评唱《颂古百则》,当然也是
十分自然的事情了。
圆悟在雪窦《颂古百则》的每一则公案和偈颂的前面加上总
论式的“垂示”,又在公案和偈颂的每一句下面附以短小精悍的
“著语”,然后分别在公案和偈颂的后面,用大段文字拈提宗旨和
交代公案的源委,给予参禅的人以很大的方便,所以当时用“丛
林学道诠要”、“留示丛林,永垂宗旨”、“欲天下后世知有佛祖玄
奥”等语赞美它。禅宗五宗七派的祖师们本来各有机用,不易
“凑泊”,自《碧岩录》出而有“敲门砖”可寻,禅风又为之一
变,因而引起当时一部分禅师们的愤慨,《禅林宝训》卷下引心
闻昙贲禅师之说云:
天禧间,雪窦以辩博之才,荚意变弄,求新琢巧,
继汾阳为颂古,笼络当世学者,宗风由此一变矣。逮宣
政间,圆悟又出已意,离(厘)之为《碧岩集》,彼时
迈古淳全之士,如宁道者、死心、灵源、佛鉴诸老,皆
莫能回其说。于是新进后生,珍重其语,朝诵暮习,谓
之至学,莫有悟其非者,痛哉,学者之习术坏矣。
心闻禅师和道宁禅师等虽然不同意《碧岩集》的作法,可是“新
进后生”护拥它。据延枯年间径山住持希陵的《碧岩录后序》
云:“大慧禅师(圆悟的弟子)因学人人室下语颇异,疑之,才
勘而邪锋自挫,再鞠而纳款自降,曰:我《碧岩集》中记来,实
非自悟。”这大概就是“新进后生”护拥《碧岩录》的原因,也
由此而发生了弊病。又《禅林宝训》卷下云:“今人杜撰四句落
韵诗,唤作钓话,一人突出众前,高吟古诗一联,唤作骂阵,俗
恶俗恶,可悲可痛。”这或者可以说是更大的一种流弊了。因此
大慧禅师要把《碧岩录》的刻版毁掉,企图杜绝“不明根本,专
尚语言,以图口舌”的禅病。
不过,大慧禅师并没有能够杜绝这种“禅病”,因为毁版之
后不久,就重行刻版,而且在重刻的《序》、《跋》上有这样说
法:
圆悟顾予念孙之心多,故重拈雪窦颂;大慧救焚拯
溺之心多,故立毁《碧岩集》。释氏说一大藏经,末后
乃谓不曾说一字,岂欺我哉。圆悟之心,释氏说经之心
也;大慧之心,释氏讳说之心也。禹稷颜子,易地皆
然,推之挽之,主于车行而已。
立语虽似调和,而用意则为《碧岩录》张目,说明《碧岩录》的
影响并未因大慧毁版而有所动摇。为什么?我以为应该研究一下
心闻禅师所说的“笼络当世学者”一语。
禅宗的集大成者慧能禅师(即六祖)本来是一个不识字的
人,出世之后,为了直指心性,语句都很质朴平实,后来的禅师
们如青原、南岳、马祖、石头、百丈、药山等等,、都亲自开山种
地,参加劳动,所用语句也大都开门见山,质直无华,所以只要
机缘凑合,村姑野老也可因而悟道。如马祖位下的凌行婆和以后
的台山婆、烧庵婆等,见地透彻,机锋灵活,并不让得道的高
僧。可见当时的禅风,比较接近于人民大众。后来禅宗的影响不
断扩大,士大夫们逐渐被吸引到禅宗方面来。冠盖莅临禅门的次
数愈多,村姑野老们自在参禅的机会就愈少,到了北宋,禅宗门
下,除了禅和子以外,就只见士大夫们憧憧往来,很少有村姑野
老们的足迹。翻开《雪窦禅师语录》,就可以见到雪窦禅师和曾
公会学士的交谊之深,和驸马都尉李文和、于秘丞、沈祠部等也
常有往还,他的荣任雪窦寺住持,就是出于曾公会的推举。圆悟
禅师和士大夫们的来往更密,他经常为运判、侍御、待制、朝
散、安抚、少保、典御以及贵妃、郓国大王、莘王、济王等达
官贵人上堂说法;历任名刹的住持,也都出于士大夫们的推举。
士大夫们鄙视劳动,爱好“斯文”,所以禅师们就不得不抛弃
“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锄头,拈起吟诗作赋的生花之笔来了,
所谓“笼络当世学者”似乎可以从这里去体会。
这样说,并不是否定禅宗史上的这一个发展,而是说明,自
唐末至北宋,由于禅师们逐渐脱离人民大众以笼络士大夫们,禅
风由质朴而变为讲究修饰语句,影响所及,极为深远,愈到后来
就愈甚。这里不妨再举两个例子加以说明。
一个例子是:著名的禅师舞文弄墨,一般禅和子们也依样画
葫芦。如雪窦禅师在杭州灵隐寺上堂说法,有僧问:“宝座先登
于此日,请师一句震雷音!”师云:“徒劳侧耳。” (僧)进云:
“恁么,则一音普遍于沙界,大众无不尽咸闻。”圆悟禅师在成都
万寿禅寺上堂说法,有僧问:“宝剑出匣,海蚌初开,向上宗乘,
乞师直指。”师云:“横按莫耶全正令。”进云:“恁么,则坐断十
方去也。”师云:“七纵八横。”进云:“宝藏拨开于此日,五叶千
灯事转新。”宾主问答,都在造句用语上费了推敲,是否可以说
是“老实商量”,我以为是有问题的。大慧禅师虽然毁了《碧岩
集》的版子,可是在他的语录里,宾主问答,也是如此。如他在
临安明庆院开堂说法,僧问:“人天普集,选佛场开,祖令当机,
如何举唱?”师云:“钝鸟逆风飞。”进云:“遍界且无寻觅处,分
明一点座中圆。”师云:“人间无水不朝东。”进云:“可谓三春果
满菩提树,·一夜华开世界香。”这说明风气已成,无法改变,明
知流弊甚多,也不能不随波逐流。其实大慧禅师提唱“参话头
禅”,也无非是以“敲门砖”给发心参禅的人,首先欢迎的,可
能是士大夫们。朱熹《答孙敬甫书》中有云:
见《杲老(即大慧宗杲)与张侍郎(无垢)书》
云:左右既得此把柄入手,便可改头换面,却用儒家语
说向士大夫,接引后来学者。后见张公经解文字,一用
此法。……但杲老之书,近见藏中印本,却无此语,疑
是其徒已知此陋而阴削去之。
朱熹所说的是否真实,又所谓把柄是否指参话头而言,固然犹有
待于研究,但大慧用儒家言语向士大夫们谈禅,则是屡见不鲜。
如他有一次用佛教哲理对张无垢谈《论语》上的“吾无隐乎尔”,
张无垢初不相契,继在游山之时闻到木樨花香,大慧随口念了
“吾无隐乎尔”,据说张无垢因而豁然大悟。这一事实,不但说明
大慧禅师善于用“敲门砖”,而且把“合流”的倾向扩大到佛教
以外的儒家去了,似乎比他的老师又进了一步。所以《碧岩集》
的版子实际上并没有毁掉,毁掉的只是某一寺院里的木板而已。
另一个例子是:《碧岩集》之后,颂古、评唱的著作很多,
如宋投子义青禅师颂古、元林泉从伦禅师评唱的《空谷集》、宋
天童正觉禅师颂古、元万松行秀评唱《从容庵录》等,也都非常
有名。此外如宋法应集、元普会续集的《颂古联珠通集》四十
卷,汇集了四百二十六位禅师的三千多首偈颂,几乎对禅宗门下
流行的公案都有了解说。元道泰编集的《禅林类聚》二十卷,把
禅宗丛林里所接触得到的人物、法事和用具等等都系以历代禅师
们举唱的偈颂和法语,给了丛林负责人应用上很大的方便。清代
集云堂编次的《宗鉴法林》七十三卷,收集更广,方便也更多,
禅师们一篇在手,头头是道,几乎可以不必参禅了,宗门自此而
衰。
中国禅宗在日本——[日]冲本克已著——蔡 毅 译
禅宗是生根、成长于中国大地的中国佛教,它形成于唐代中
期,在中国全土普及后,又传人构成东亚文化圈的各个地域。现
在禅不仅在中国本土,在朝鲜、日本、越南等国也依然存续着它
古老的生命。在这些风土各异、文化互别的地域流传的禅,保持
着一种怎样的状态?这里拟对传至日本的禅做一番概观。
为了确定本文论述的角度,我想先考察一下文化传播的基本
形态。什么是文化传播?要言之,就是具有先进文化的国家或地
域,把它高度发展了的文化向其他地方移植的过程。
而接受这种文化传播的一方,因其社会状况、期待程度乃至
接受能力等种种问题的存在,对优秀文化并不一定是兼容并蓄。
而且因接受国文明程度的不同,对引进的先进文化的融汇改造,
也会呈现出复杂多样的状态。
根据这种情况,我们可以把文化传播大致归纳为以下四种类
型。首先是先进文化圈的文化,在向同样高度发达的异质文化圈
传播时,遇到的抵制、产生的磨擦大多较为剧烈,不易进行。即
使被接受了,也会在很大程度上被改造加工。具体的事例,我们
只要看看印度佛教传人中国的情形,就可以明白。中国人对这一
异国文化,开始并不那么关心,佛教在中国扎根,不仅经过了很
长时间,而且在移植过程中还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
其次是先进文化圈的文化向落后地域传播时,接受一方一般
持积极欢迎的态度,因为他们无须劳心费力,就可以获取丰硕的
文化成果。也正缘于此,接受一方会尽力保持先进文化的原状,
使其没有太大的变化。中国的佛教(禅)传人朝鲜、日本以及越
南的状况,显然属于这一类。
而落后的文化传人先进文化圈、并产生某种影响的事例,则
较为鲜见。偶或有之,也不过是先进文化圈的人们对异国风俗土
产的欣赏喜爱,所谓搜异猎奇罢了。当然,这种迥异其趣的异质
文化,可能带来新鲜感,激发想象力,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称
之为文化传播。至于落后的文化向同样落后的文化圈的传播,则
罕有其闻。
面对上述分类,想必有人会提出质疑:所谓“先进”、“落
后”的文化,其衡量标准到底是什么?这显然是一个很难回答的
问题。但不管怎样,被传播的文化之所以会发生各种不同的变
化,必然和授受双方文明程度的相对差异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当
然仅此一点还不能说明全部问题,风水土地、作为文化载体的语
言以及思维方式等方面的歧异,都会对文化接受中发生的变化起
着复杂多样的影响,这些都是我们在瞩目文化传播时必须时刻注
意的问题。
处于东亚文化圈边缘的日本、朝鲜对中国传来的文化,大致
保持着其原初形态。例如日本一直使用的中国汉字里,就至今仍
留存着不同时代的中国本土的各种读法。由此推及佛教,我们似
乎可以说,平安时代传来日本的天台、真言两大宗派,现在仍然
保持着唐代都市佛教的状态,而镰仓时代传来的禅家各派,今天
也同样飘散着浓厚的宋代禅宗原有的气息。
在日本,还有江户时代明僧隐元隆琦(1592—1673)传来的
临济禅,作为其法系的黄檗宗的独特宗风,呈现的也是当时明代
禅的形态。
传到朝鲜的,则是唐代中期处于全盛时代的禅。虽然后来随
着王朝的兴亡,朝鲜的禅也发生了种种变化,但基本的形态一仍
其旧,古风盎然。而在中国本土,却或融会念佛,或改换仪礼,
变化不断,以迄于今。
因此,如果我们能注意到禅宗从古至今的种种变化形态现在
仍留存在不同地域的这一情况,并加以深刻研讨的话,就可以切
实把握禅宗史的全貌。
佛教正式传来日本的时间,有宣化三年(538)和钦明十三
年(552)两说。在其传人初期,对庶民的教化和接触是被禁止
的。佛教在日本真正的扎根、普及,大约是五百年后平安末期至
镰仓初期的事。有趣的是,在中国佛教史上,包括禅宗在内的各
种中国式的宗派的成立,恰好也是佛教公传后五百年的事,两者
偶然相合。在中国,东晋时代频仍的战乱,使人们开始对人生产
生怀疑,并对死后感到不安。为了解除这种苦恼,佛教于是受到
崇奉。在日本,也是人们苦于平安末期的战乱和饥馑,因而向佛
教寻求救助。可见佛教思想从传人到成熟,无论在中国还是日
本,都需要一定的时间和条件。
在日本,适应庶民的要求而得到迅速发展的,是独特的念佛
系统的佛教。从中国大陆输人的禅宗,开始只受到王侯贵族的青
睐,却不能满足普通民众对宗教的渴望。直到禅宗也像密教、净
土真宗那样注重死后往生和现世利益,采用简便的实践方式以及
咒术以后,才被普遍接受。
综观佛教史,我们似乎还可以做这样的概括:产生于印度的
佛教,因受印度独有的思维方式的影响而形成了密教;中国的佛
教则因受儒教、道教的深刻影响而形成了禅宗;同样,传来日本
的佛教和本地的思想结合而形成了净土真宗。这些宗教形态,都
与其产生地的风土息息相关。因此,现代日本虽然有纷杂众多的
佛教宗派,究其内在本质,其实有很多地方是彼此相通的。
一般认为,最先把中国禅传回日本的,是法相宗的道昭.
(629---700)。他人唐承慧可的弟子慧满传授禅法,但他只是作为
“三学”(戒、定、慧)之一予以接受,其禅观并没有在日本单独
流传。其后是北宗大通神·秀(6067--706)的弟子普寂(651—
739)门下的道培(702--760)的来日。但他也只是作为南都六
宗(南都指奈良,六宗为早期日本佛教宗派:三论、成实、俱
舍、华严、法相、律宗)之一的律宗初祖在佛教史上留名,同样
没有在日本留下传播禅的记录。就中原委,我想大概是因为禅宗
思想本来是为了否定难解的教理而以简明达意为实践中心而产生
的,这对处于佛教传人初期的日本人来说,理解上暂时还有困
难。
道培的律和禅的系谱虽然还只是形式,但传于最澄(767—
882),却成为他人唐求法的动机。最澄也从中国传回了禅,但同
样没有得到当时宫廷的理解。较之艰苦的修行和难懂的解脱理
论,当时日本的贵族们对实在的关乎现世利益的咒愿,要更为欢
迎。
佛教传来日本后,随着社会的进步而逐渐成熟,以此为基
础,到了镰仓时代,禅的地位也得以确立。在中国历经兴亡的禅
宗五家七宗之中,传来日本的是临济宗和曹洞宗,它们各自经过
不同的发展道路,一直走到今天。
传布临济宗(黄龙派)的荣西(1141—1215),原来是天台
宗的高僧。他人宋的目的,是为了使综合各个宗派的佛教得到复
兴。传布曹洞宗的道元(1200--1253)也是个雄心勃勃的青年。
面对时代的不断更替,他希望用新的佛教思想来改变日本佛教的
面貌。他为了反对因受王侯垂青而兴盛的临济宗,决意到远离京
城的越前(福井县)建立永平寺,以发扬纯粹的禅的精神。水平
寺的建筑,是仿照了道元曾留学过的中国天童山景德禅寺的样
式。可是,在日本开始独自发展的日本达摩宗的信徒们,因受到
弹压而逃散到各地,有的融人曹洞宗,使道元的宗风很快就面临
着被改造的危机。他晚年过激的批判态度,正反映了这一背景。
规矩刻板、修行严格的枯淡的曹洞宗,一度曾陷于衰亡的绝
境,但莹山绍瑾(1268—1325)的出现,他对密教注重现世利益
的方法的大胆吸收,又使曹洞宗转趋隆盛。禅在日本,就是这样
一方面保持着其传来时的形态,一方面又受到各种日本式的改
造。
在上述情况发生前后,随着南宋的灭亡,许多禅僧亡命来到
日本。、他们有所谓二十四流四十六传之称,内容十分丰富多彩,
但来日禅僧们也良莠不齐,玉石混杂。
禅本来重视个性,讲求依照个性发扬宗风,因而日本的各个
流派都个性独具,没有相同的面目。其间虽然也有竞争淘汰,如
吸收临济宗杨岐派流风的大应国师南浦绍明(1235—1308)、大
灯国师宗峰妙超(1282--1337)、关山慧玄(1277—1360)等被称
为“应灯关”的流派最终占据了主导地位,但其他流派并未因此
而舍弃自己的原有名称。因此,临济宗至今仍然分为各以其本山
寺院为名号的十三个流派。这些流派从本山到其下属的一般寺
院,都十分重视维持各自的法系,即使是新人寺的住持,也要遵
照惯例改承本派法系,这叫做“伽蓝法”。而住持自己有原先出
家接受指导的老师,这叫做“人法”。像这样具有不同的两种法
系的情况,是很普遍的。中国的寺院本是十方住持刹制(招聘与
本法系无关的优秀僧侣的制度),而在日本,则变为重视传统继
承的一流相续制(本法系弟子为后继者的制度)。
在这以后,隐元隆琦于1654年来日。他以杰出的号召力,
使日本禅界靡然从风,妙心寺派(临济宗)曾一度想请他担任管
长(宗派领袖),但受到愚堂东宴(1579---1661)的阻止。隐元
所传的临济禅,于中国本土已经在仪规等方面发生了种种变化,
因此它和日本仍顽强保持着宋代风习的应灯关的禅虽然同属临济
宗系统,却互不相容,形同水火。隐元于是离开妙心寺,到宇治
仿照中国故地的样式,新创了黄檗山万福寺,是为黄檗宗。
此后又有白隐慧鹤(1685—1768)登场。他根据自己的体
验,建立了新的公案禅体系,并完成了日本式的新仪规。简言
之,就是仪式的简略化和坐禅方法的变更,以及密室的参禅。这
样,传统的面壁参禅,变为对面而坐;公案的问答应对,也从在
大众面前公示,变为师徒二人在室内秘密进行。而且这些都是在
短时间内激烈的修行中集中完成的。此后,临济宗的各个流派便
都遵从这种以“悟”为至上命题的方法。
有人认为,后来又出现了把禅与念佛结合起来的“妙好人”
(对笃信净土真宗者的赞语。其特点是对信仰绝对皈依,对环境
绝对顺从)。其实,他们这种随顺万物的做法,应该看作是为了
加深念佛体验,而和日本人委运乘化的“自然法尔”思想的结
合。那种认为既然一切事物都可以从禅中得到解释,那么万事万
物就无不是禅的看法,其实是世俗化了的禅思想,并非正宗。
同样的情况也表现在各种艺术中。在日本,人们对于那些和
禅一起兴盛起来的茶道、花道、绘画、建筑、武术等诸般技艺,
往往习惯于到禅里面寻求其精神内蕴。而把这些本来属于世俗的
文化现象,和本质上是否定性的宗教——禅简单地扯在一起,应
该说是错误的。
明治初期,发布了维护国家神道的“神佛分离令”,其目的
是要以神道为国家指导思想,抛弃佛教。日本于是掀起了史无前
例的废佛运动,各地寺院被大量破坏。
稍后颁发的“太政官布告第百三十三号” (1872),还宣布
“自今僧侣可随意食肉、娶妻、蓄发,除法要行事之外,穿着可
与一般民众相同”。其意图本来在于放弃国家对佛教的管理,但
佛教徒们却趁此机会,把它当作官方对佛徒同俗食肉娶妻的认
可,在这以后,僧侣就公然娶妻,毫无顾忌了。
其实,日本由镰仓时代创立净土真宗的亲鸾(1173—1跖2)
肇始,就有所谓“非僧非俗”的说法。而江户时代以来,由于有
为了抵制基督教势力而建立的寺院担保制度,寺院成为所在地的
居民管理机构或文化活动场所,其自身的经济收入因而得到保
障。与此同时,一部分僧侣秘密娶妻,即所谓私养“大黑”(大
黑天,七福神之一)的行为,也应运而生。
这种戒律的空洞化现象,如果追根溯源,可以找到很多历史
和现实的关联因素:自最澄以来,日本就有只要受持大乘戒经
《梵网经》所说的菩萨戒,就承认他是僧侣的风习;在真宗以外,
也同样存在着对那些以禅主张通达圆融、不拘小节为理由而鲜廉
寡耻的行为给予容忍的倾向;加之封建农耕社会独具的平均思
想,使村民中难有特立异行之土——凡此种种综合作用,使日本
佛教产生了上述特异的现象。
佛教在传来日本的每个阶段,都同时带来了中国的各种文
化。那些舶来的珍贵文物,曾令日本人惊喜万分,对日本文化的
发展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禅宗作为中国文化的精华之一,也带来了大量的制作技术、
艺术形式乃至生活用品。这些中国文化的传人,与当时日本城市
的发展、代表新兴势力的市民的兴起相适应,从而给他们的生活
文化以深刻的影响。例如椅子、暖帘、蒲团等生活用具,纳豆、
豆腐等食品,“普请”、“人事”、“单位”等用语,都是和禅宗一
起传来日本的,这些不胜枚举的文化现象,今天仍然广泛渗透在
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
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禅宗传来的葬礼仪式和对死者的追
善供养。佛教本来与葬礼无涉,僧侣的安葬仪式十分简朴。但在
中国禅宗兴盛的唐代中、后期,由于俗世信徒的增加,他们还希
望有佛教式的葬礼,于是在几乎全面吸取儒教仪礼的基础上,产
生了现今葬礼的原型。这种葬礼巧妙地吸收了六祖慧能提倡的被
称作“无相戒”的简易大众授戒法。戒律规定非佛教徒不能举行
佛教葬礼,但如果对死者施行死后授戒,就合规中矩,不算违
例。具体做法是在死者遗体前唱忏悔文,授与三归依戒,然后再
授菩萨戒,赐以出家戒名。程序完成后,即举行葬礼。
追善供养则是举行各种盛大的死者祭奠仪礼。具有供养先祖
意义的彼岸会、施饿鬼会等仪式,本来并不是禅宗的专利,日本
古已有之。但随着佛教式葬礼的普及和大众化,死者葬礼和先祖
供养被融为一体,渐渐在日本习俗里扎下根来。
禅宗容易被认为是以坐禅为宗旨,其实坐禅固然重要,但禅
宗另一方面又主张行住坐卧时时皆禅,而对那种单纯修行的坐禅
持否定态度。这种既鼓励坐禅、同时又否定拘守坐禅的难以解释
的玄妙旨趣,和普渡众生的现实要求之间,可以说正体现了禅宗
在大众化过程中明显具有的基本矛盾。而禅宗的影响,实际上在
偏离其宗旨本质的各种文化方面,表现得要更为显著。
佛教的分类也是方法多样,不一而足。大乘和小乘(上座
部)有别,这已为人所熟知,在日本还常有“自力门”(圣道门)
与“他力门”的区分。净土教信奉弥陀的绝对他力,禅宗则主张
以自己的力量来努力严格修行。这种对立中所隐含的,是认为自
力脆弱浅薄、不足凭依的他力门的价值观。
然而,现在日本的佛教如前文已指出的那样,尽管在教义、
行事等表面的理念、方法上,各有其独自的特性,其实各个宗派
内里颇多相似互通之处。这主要是为了适应檀家制度(民众皆为
寺院施主、信徒)和民众对均一化的要求,而死者仪礼、先祖供
养的方法因宗派不同而大相径庭的情况,也确实令人无所适从。
从这种互相融合的过程中,日本佛教的特点以及日本人独特的文
化和思考方式,也可以略见一斑。
这里再简单谈谈禅的思想。禅本指佛教的一般实践,从达摩
开始,转化为指禅宗这一宗派。禅宗信徒们还把自己的信仰称作
“宗教”。所谓宗教,是指终极真理(宗)的语言表现(教),而
终极真理本来是不能用语言表现的,所以宗教这一现象,其本身
原已处于矛盾的境地。对这种矛盾,禅宗的基本立场是主张不是
用语言的教理体系,而是试图用信仰的实践来加以扬弃。
此后定型化了的四句格言:“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
心,见性成佛”(不依据教义或经典,直视对方内心,使之顿悟
禅的本质),把禅宗的这种态度表现得更为充分。这里虽然也有
对语言的否定,但其所否定的,是那种确定性的结论,或从对立
的两项概念中选择正误的理性主义观念。而对此外的语言行为,
如诗文、破坏固定观念的“非、不、无”等否定词汇,或象征性
的表现,禅宗非但不否定,毋宁说用得更多。历来的宗派,都是
用语言阐述自己的理论体系,但是禅宗对此表现出强烈的反讽和
排斥,其于思想史的意义,正在这里。
因此,为了在日常生活中实现佛法,禅宗还创造出一种把具
体场景作为“公案”,用于教导后学的独特的修行方式。在现代
的僧院生活中,这种方法仍显示着它的生命力。
禅被看做是东方思想的代表形态之一。其非合理性的神秘主
义、体验主义的思维和实践,曾被认为是可以解救以“上帝死
了”为标志的西方近代理性主义于绝境的一剂良方。其实,东西
方思想本来并非隔绝不通,截然两样。不过是各自所处的环境和
时代不同,因而什么思想被优先选择和什么思想被视为重要,也
就随之不同罢了。
与希腊哲人们会享思想的盛宴相仿佛,在印度是《优婆尼沙
陀(奥义书)的自由思想家们的活跃,在中国则是春秋战国时
代的百家争鸣。广阔的东西方思想舞台上,从唯心论到唯物论,
从厌世哲学到享乐主义,各种思想施展身手,层出不穷。概言
之,可以说西方偏重二元论,而东方侧取一元论。在现代文化
上,这既表现出两者的重大差异,同时在现代频繁的交流中,又
起到互补共进的作用。
然而,目前这些思想和文化,还只是在各自的领地矛盾杂处
而已。能否在更高的层次上把它们加以整合?这是今后必须解决
的课题。禅宗的本质,是不固守既有的体系,其思想、实践均以
现时的存在为出发点。因此,对于上述课题,禅宗在具有内在矛
盾的同时,也显示了提供某种解决方法的可能性。
日本近代禅学研究者中,著名的有忽滑谷快天(1867—
1934)、宇井伯寿(1882--1963)等。他们是涉猎广泛的佛教学
者,但又是曹洞宗的僧侣,因此他们关于禅的研究,主要着眼于
曹洞宗。临济禅的代表人物有铃木大拙(1870--1966),他致力
于向欧美介绍禅学,在敦煌禅籍的研究上也贡献厥伟。
可是,学问和宗教本质上原是矛盾对立的。因为学问以
“疑”为动机,追求的是思辨性世界的证明;宗教却以“信”为
动机,憧憬的是超越性世界的翱翔。铃木大拙是优秀的禅徒兼学
者,就很遗憾地显露出兼两的界限。铃木还是日本独自的哲学
——西田哲学的创始人西田几多郎的朋友,他对西田“绝对无”
思想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
当代对禅宗语录的解读成就卓越的有人矢义高,此外柳田圣
山、镰田茂雄等也有关于禅学的优秀研究成果问世。
中国现有的寺院以及佛教遗迹,几乎都与禅宗有关。这也是
最后全部归结于禅宗的中国佛教史的必然结果。每年有很多日本
的僧侣、佛教徒和学者为了研究或参拜前往访问。寺院香火的复
兴,给人以深刻印象。我们衷心期望中国禅寺更加兴盛,日中禅
学交流不断发展。
西方的禅——[美]艾伦·沃茨著——徐进夫 译
想要吸收像禅这样极具中国味的东西,对于盎格鲁撒克逊人
跟日本人并无二般:同样困难。因为,尽管“Zen” (禅)之一
字,是日文的读法,而日本现在又是它的家乡,但禅宗或禅学却
是中国唐代创始的东西。我如此说,并非想要琐屑唠叨地数述不
可数述的异国文化的隐微之处。问题很简单:自觉亟需自辩的
人,想要明白无此需要之人的观点,并不是一件容易办到的事。
而创始禅宗或禅学的中国人原是与老子同类的人,而老子在距今
二十余世纪以前就曾说过:“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因为,
无论是想要使得自是还是想要证明白是这种冲动,一向总会引起
中国人的好笑、荒唐,或滑稽之感,此盖由于身为儒家兼道家的
中国人,一向总是欣赏“述而不作”的人。对于孔子而言,合乎
人情总比合乎天理好些;对于伟大的道家老子和庄子而言,则显
而易见的是,有是必有非,因为此两者表里相关,不可分故。正
如庄子曾经说过的一样:“迕道而说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
骤而语形名赏罚,此有知之具,非知治之道。”
在西方人听来,这些话也许有些讥刺,而儒家的“讲理”和
折衷,亦不免有些优柔寡断,缺乏原则。但是实在说来,他们对
于我们所谓的自然的平衡,亦即人与非人之间的均衡反映出一种
奇妙的认识与尊重——把人生视为自然之道的一种宇宙的生命
观。在这当中,善之与恶,成之与毁,智之与愚,皆属不可分离
的存在极性。《中庸》有言:“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
也。”因此,智慧不在强行排恶取善,而是学习“驾驭”它们,
亦如浮木之随波上下,对于一个人的本性上的善恶,中国人的生
命根柢中,且有一种特殊的信心,这是在从希伯来到基督教文化
的慢性良心不安中成长的人感到特别陌生的一点。然而,在中国
人看来总是显而易见的是:一个怀疑自己的人即使对他自己的怀
疑也不会相信,故而也就只有乱成一团了。
过去二十年来,西方人之所以日渐对禅发生特别浓厚的兴
趣,原因不止一端。禅宗艺术对现代西方心灵所产生的魅力,铃
木大拙的著述,以及一种非概念式的体验哲理在科学相对论的风
土中所受到的注意——所有这些,莫不皆有关联。还有,不妨在
此一提是,禅与诸如维特根斯坦哲学、存在主义、一般语意学、
沃夫(B.L.Whorl)创造的玄妙语言学以及科学的哲学与心理
治疗方面的某些运动等等纯粹西方趋向之间的相似性与亲和力。
背地里,我们的心里总是有着一些隐忧:对于基督教的不自然或
与“反自然”两者,对于它那有着政治秩序般的宇宙论以及科
技,对于它对使人类感到怪异的自然世界所作的一统式的机械
化。因为这两者都反映了一种心理:人与一种意识上的智力认
同,而意志则在自然的外面控制自然,就如人类的形象多依建筑
家构造上帝的形象一样。这种隐忧起于这样的一种怀疑:尝试从
外部主使这个世界的企图是一种恶性循环,并以此为永无穷尽的
控制、控制(controilling controilling)与监督、监督(supervising
supervising)而惶恐不安,永无了期。
对于寻求恢复人与自然合一的西方人,禅似有一种超过泛神
论甚远的吸引力,存在于自然之中——存在于马远与雪舟的山水
画中,存在于一种既是属灵的又是世俗的,以自然的方式传达神
秘的奥义的,尤其真实的是,从来没有想到真俗不可并存的艺术
之中。对于在精神与物质、意识与潜意识方面一向有着重大分别
的一种文化,这里有一个可以提供深切而又清新的完整之感的世
界观,存在其中。因此,中国的人本主义与禅的自然主义深深地
吸引着西方人,远远地胜过印度佛教或吠檀多(Vedanta)哲学。
印度佛教和吠檀多哲学在欧洲虽亦不乏学者,但大体而言,它们
的追随者似乎只是一些转换了的基督徒而已——只是一批寻求一
种比基督教超自然主义更能言之成理的哲学,借以推行本质上是
追求神迹的基督教方案的人们罢了。印度佛教的理想人物显然是
一种超人,一种绝对掌握自性的“瑜伽徒”(yogi),与科幻小说
的理想人物、“超于人类的人”完全一致。而大觉佛陀或悟道的
中国禅人,则是“平常人”,毫无奇特;其幽默风趣而富于人味
之处,宛如牧溪和梁楷所绘的禅颠。西方人们之所以喜欢这些人
物,乃其有史以来第一次在这里得到一个概念:圣人和哲人并不
是遥不可及的人,只是完人而不是超人,尤其重要的不是一本正
经的禁欲主义者。尤胜于此的是,禅之觉醒吾人与宇宙“本不可
分”的开悟经验,不论多么难以捉摸,总是不离当处,就在目
前。
我认为,禅之所以在后期基督教的西方得着许多人的好感,
因为它既不讲经说法,更不以希伯来基督教一线相关的先知作风
对人说教和责斥。佛教并不否认,艺术与科学、理性与善意,对
人类的生活可有相对有限的改善境地。不过,尽管它认为此一活
动境地非常重要,但对于过去、现在,以及未来三世万法皆如的
那个比较无限的境界而言,却是附属的、次要的。因为,这个境
界完全超出善与恶、成与败以及个人健康与疾病等等的范畴。
希伯来基督教的宇宙,为道德的迫切、正义的热切、包括一
切、贯串一切的世界。作为绝对本身的上帝,就是与恶互不相容
的善。因此,不道德或非正义,就使人感到自己是个被放逐的人
——不仅被逐出人类的社会,同时亦被逐出存在的本身,被逐出
生命的根基。因此,一个人一旦犯了错误,就会导致一种形而上
学的焦虑和罪恶之感——一种永远受到处罚的境地——与他所犯
的过错完全不成比例。这种形而上学的罪过实在太难成立,令人
太难忍受了,最后必然会有使得上帝及其律法遭受反对和排斥的
一天——而这正是现代现实主义、唯物主义以及自然主义等等整
个运动所发生的情形。绝对的道德对于道德具有深切的破坏性,
因为它所用以对付罪恶的罚则实在太重、太重了。人们不能因噎
废食,不能以砍头的办法治疗头痛。禅的吸引力,跟东方其他哲
学的魅力一样,乃是:在善恶的紧迫境域背后推出一个广大的自
性境界——一个不但不必再有罪恶或遭受谴责之事,而且最后终
于可使自己与上帝不别不二的境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