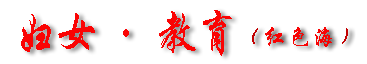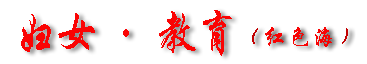|
|
| | |
| | 淡泊人生花为友——萧淑芳
| | | | 6月4日至9日在北京国际艺苑美术馆举办的“萧淑芳九十以后新作展”上,这些萧先生90岁以后创作的花卉作品吸引了人们的眼光。
萧淑芳:淡泊人生花为友
百合、萱草、金莲花、太阳花、火鹤兰、虞美人,还有许多叫不出名字的花,它们在萧淑芳先生的作品中,生动别致,清新绚烂,具有灵性之美。
“人生是一次旅行,有泥泞黑暗,有险峰……尽管有过许多曲折和磨难,但毕竟春天会来,花总会开。”如她的作品一样,一生历经风霜的萧淑芳始终以“恬适明净之心”漫步在春天里,邂逅在百花间。
情系绘画
萧淑芳于1911年出生于天津,在姐妹7人中排行老五。自幼她就“喜欢世间美的事物”,在绘画方面显现出很高的天赋,“画什么像什么”。她经常把各种故事画成画儿给妹妹,还因为在课堂上偷偷画画儿并传给同学看,而被老师罚了站。
父亲萧伯林看见女儿的画后,称赞她的手是“宝手”,不仅请名师给她进行指点,还特邀艺术大师齐白石先生为她治印。15岁那年,萧淑芳经由她的叔父——我国现代音乐的奠基人之一萧友梅推荐,进入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西洋画系学习。3年的系统学习奠定了一定的绘画基础,萧淑芳作为旁听生进入中央大学艺术系徐悲鸿工作室学习油画和素描。同时,她还得到汪慎生、汤定之和陈少鹿三位名师的指点。
1937年至1940年,萧淑芳到瑞士、英国、法国学习油画和雕塑。在这期间,她把中西方不同的艺术形式和风格融会贯通,兼容并收,创造了自己独特的绘画技巧。
在追寻艺术的道路上,萧淑芳深知生活对于艺术创造的重要。上世纪50年代,萧淑芳有机会经常深入基层。那时候,她就发现,“祖国虽然解放,但是很多劳动者过着疾苦的生活,我对劳苦大众从心底更为尊重,这对我一生很重要。”
从此,萧淑芳的画笔着重描绘具有时代特征的人物和各种美的事物。她两度作为石窟考察团中唯一的女性赴炳灵石窟和麦积山石窟;作为唯一的女艺术家参加绘制新中国的第一幅大型壁画——北京天文馆藻井壁画;作为唯一的女画家第一个到煤矿巷道体验生活,创作出许多以煤矿工人生活为题材的美术作品……
但替河山添彩色
文化大革命以后,在中央美院任职的萧淑芳被调到国宾馆画一些风景、花卉的画。从那以后,她就开始真正画花。“花开花落,带给人们许多对生命的感悟,所以,我爱花,画花。”
萧淑芳的花卉画在题材选取上极具个性。她喜欢画的花卉大约有四五十种,如紫鸢、绣球、扶桑等几乎全是野花,而她从不画牡丹等大富大贵的花。
老人解释说:“我画花喜欢画山花、野花,它们有顽强的生命力,而且这些花很少有人知道,把它们表现出来让人欣赏,我特别高兴。”
吴作人先生生前有感于萧淑芳充满真情与执著地描绘野花,曾作诗一首以表敬意:“边陲奇卉遍山生,风雪霜寒志更贞。但替河山添彩色,不争谱上百花名。”紫色是萧淑芳的最爱。在萧淑芳的画中,表现最多的是鸢尾花。因为自由自在地生长在东北沼泽边缘的鸢尾花颜色为深紫色,而且每一朵鸢尾花都呈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和绰约的丰姿。
萧淑芳研究出的紫色是一般人很难调配出来的,似乎成了她色彩的专利。为了突出带有飘逸感的花朵,她删繁就简,有意将长而繁多的叶子加工为疏密有致的短小状;画面洋溢着令人赏心悦目的质朴与美丽。
中央美院孙美兰教授评价萧先生的作品是“极度单纯简洁”,“将数不尽的花朵和美的生命,从宇宙间捕捉了下来。简约之笔,堪与白石老人晚年画虾、吴作人晚年画金鱼媲美。”
与夫君携手半世纪
在萧淑芳的艺术道路上,她并不寂寞,因为有丈夫吴作人一路同行。
师从徐悲鸿期间,萧淑芳和吴作人是同班同学。那时的吴作人留给萧淑芳仅有的印象是“十分腼腆”。每晚在明灯高悬的画室里默默地画画儿,“不爱理人,给人一种高傲之感。”不久,二人各自去国外留学,就此分离。
直到1946年,上海美术作家协会举办的画展开幕那天,吴作人作为组织者迎接参展画家时,才与当时在上海市立专科学校担任美术教师的萧淑芳再次相见。
经历了17年的风风雨雨之后,两位老同学见面倍感亲切,心灵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为此,吴作人特地作了一首题为《胜利重见沪上》的诗:“三月烟花乱,江南春色深。相逢情转怯,未语泪沾襟。”两年后,两人喜结连理。徐悲鸿、廖静文夫妇光临婚礼,并欣然担当他们的证婚人。徐悲鸿还画了一幅水墨画《双骥图》当作贺礼。《双骥图》的画面上是一对昂首飞奔的骏马,斜首顾盼,腾空飞跃,寓意二人在今后漫长而曲折的人生道路上比肩奋进。
从1948年到1997年,近半个世纪的时光里,吴作人和萧淑芳始终牢记恩师的厚望,“互相切磋、互相帮助,互敬互爱。”
在吴作人去世前一直生病卧床的6年中,萧淑芳从为她穿衣、洗脸、洗澡、喂饭到推着轮椅陪他散步,始终在他的病榻前守候,连心爱的画笔都未曾拿起。她笑着说:“为他作出牺牲,我心甘情愿。”回忆起曾经的岁月,老人布满皱纹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吴作人的遗体告别仪式上,他的身上盖的白锻中间是一个“寿”字,四周缀以朵朵红梅。这是萧淑芳特地亲手绘制的《寿梅图》,她说:“作人小字‘寿’,我小字‘梅’,合为一体,生死不离。作人的遗体火化时,让我这颗拳拳之心跟着他的灵魂一起飘向云霄,随其左右,自由飞翔!”
萧淑芳的生活是永远不会失去追求的。丈夫去世后,她又重新拾起了画笔,投入到新的创作中去。
萧淑芳的孙女吴宁说:“她的身体不是很好,但是她只要一画画儿,身体就好了。”萧淑芳在90岁以后的3年间,笔耕不辍,画了200余幅花卉画。
中央美院艾中信教授佩服地说“我给萧淑芳先生起了个名字叫‘百花之友’。一般来说画如其人,画品跟人品也是一致的。概括萧淑芳的话几乎都可以把最美好的词放在她身上,但是我觉得最美好的一点是真诚。”
萧淑芳先生将自己一生为艺术的执著求索淡化成“走过九十”四个字。回首今生,老人淡然地说:“虽然我对国家和社会的奉献很微薄,但我是尽了自己的力量去做。”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