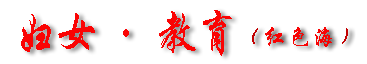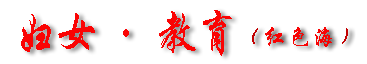|
|
| | |
| | 上海新女性
| | | | 上海新女性最重要的特点,是独立性,而且是比以往更进步了的独立性。要说女性的魅力,独立着的女性魅力更大。
关于女性的独立,早在上世纪初的“五四”时期,就是一个热门话题。当时提出许多妇女问题,女性的人格独立是其中十分重要的方面。但中国女性真正的独立,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开始实现,而且实现的过程非常艰难曲折。不过,上海女性的独立,由于众多的有利条件,总是走在中国女性的前面。
谈起上海的女性来,常会产生羡慕的心情。羡慕的内容很丰富,有对上海女性容貌的赞美,对她们时髦的穿着打扮的称颂以及对她们现代色彩颇浓的情调的欣赏等等。但最为羡慕的,是上海女性具有的独立性,认为这是上海女性最得天独厚的地方。独立性,这确实是上海女性的骄傲。多年来,为外地人所津津乐道、上海人也并不避讳的“上海小男人”,就是与这种骄傲有关的。在外地人的眼里,上海的男人在自己所爱的女性面前格外顺从。尤其在家里,一切都由她说了算。外地人的这种眼光,实际上已经被不分内外的人们所公认。这就是上海女性独立的明证。如果女性是依附于男性毫无独立可言的,那就是倒过来顺从的问题。这主要在家庭生活中,女性因为勇敢又有效地独立着,而男性却既没有独立的行动,也没有独立的愿望,就只得乖乖地顺从女性了。
上海女性的独立现象,是打着时代的烙印的。在改革开放之前,虽然在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中,也有一些上海女性独立意识很强,但还没有在整体上形成气候。她们的这种意识以及由此生发的行动,凶猛虽然凶猛,但比较多地局限在家庭的范围。而今天,女性在家庭中的独立固然不在话下,在社会生活中,这独立已经势如大潮,很显得汹涌澎湃。在各个领域,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我们随处可以见到独当一面的女性。她们思维敏捷,行动果敢,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建设中奋进不息。有的不仅带领着女性,还指挥着男性。这无数妇性的独立形象,构成上海新女性的标志形象,是上海这座国际性大都市里非常亮丽的风景线。
女性的独立现象,就个人说,是人的个性最充分的展示;就社会说,是一种时代精神的总体的反映,是优越的外部环境使一种特殊的人格力量得以不断地萌生、积聚和贡献。这是说,新女性的独立性,是时代精神和开放社会的产物。这样的新女性,在上海层出不穷。笔者认识这样一位女性:她才30岁出头,却已经是上海颇有知名度的两家民营装潢设计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个人已经拥有千万资产。她曾经绘声绘色地向我讲述她十年来的奋斗史。她本来并不独立,在丈夫经营的公司里当助手。改革开放的形势,生意场上令人跃跃欲试的机会,给了她独立作战的勇气与信心。她再也不愿意在丈夫的大树底下乘凉,她觉得那样不能尽情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于是她就自己独立注册了公司。不独立则已,一独立,连她自己也不无惊讶,竟然闯出了一个又一个新天地。她说,她虽然个性很强,但如果没有一种形势逼人又造人的客观环境,她是不可能独立的。而独立之后,她觉得无限痛快。因此,她对催起和铸造她独立性的环境充满了感激之情。
这位年轻的女企业家享受着独立之后的痛快。但是,后来我又听她说,她的非常痛快只是一个方面,她还有许多难以尽述的痛苦。她的痛快是用她的痛苦换来的。比如,她十分繁忙,繁忙到她很少回家。她把自己绝对心爱的儿子扔给了母亲,她与丈夫难得见面,她不断地听到丈夫的抱怨。她有许多诸如收藏、运动、休闲之类的爱好,都因为没有时间而只得放弃。不仅是她,我曾经与一些同样有独立性的女性交谈,她们几乎都有与这位女企业家类似的痛苦。由此,我想到,女性的独立诚然美好,但美好的东西不可能轻易具有,它要付出一定的有时甚至是沉重的代价。可是,人们光是看到新女性的独立性燃烧着的光芒,却不曾想到她们用以燃烧的燃料其实是她们日复一日的汗水与心血。
女性的独立,既可体现在家庭中,也可体现在社会里。前者的体现不大会造成痛苦,后者的体现则是免不了痛苦的。而社会生活中的独立,反映的是独立性在更高层次上的进步,于是,新女性的独立呈现出复杂性。现实的情况是,如果女性的独立性一味地体现在自己的家庭里,一般就不大可能在社会生活中再去体现;反之,如果女性在社会生活中充分地体现了独立性,往往在家庭中难以保持独立的地位。一位伟人说过:“一切都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以时间论,叱咤风云于社会的女性,必然时间紧张;以地点论,日以继夜地工作,人总不在家;以条件论,每天在社会上忙得晕头转向,哪里还有剩余的精力来维持家庭中的独立?既然如此,家里的独立性只好“转移”,大权旁落,甚至只好无可奈何地依附于自己的男人。于是,现在一些非常能干非常独立的女性,在家里往往是另一种形象。看来,女性,即便上海的新女性,要彻底地实现自己的独立也难。从这点上说,也可以说人往往具有两重性,谁也难以避免吧。
| |
|